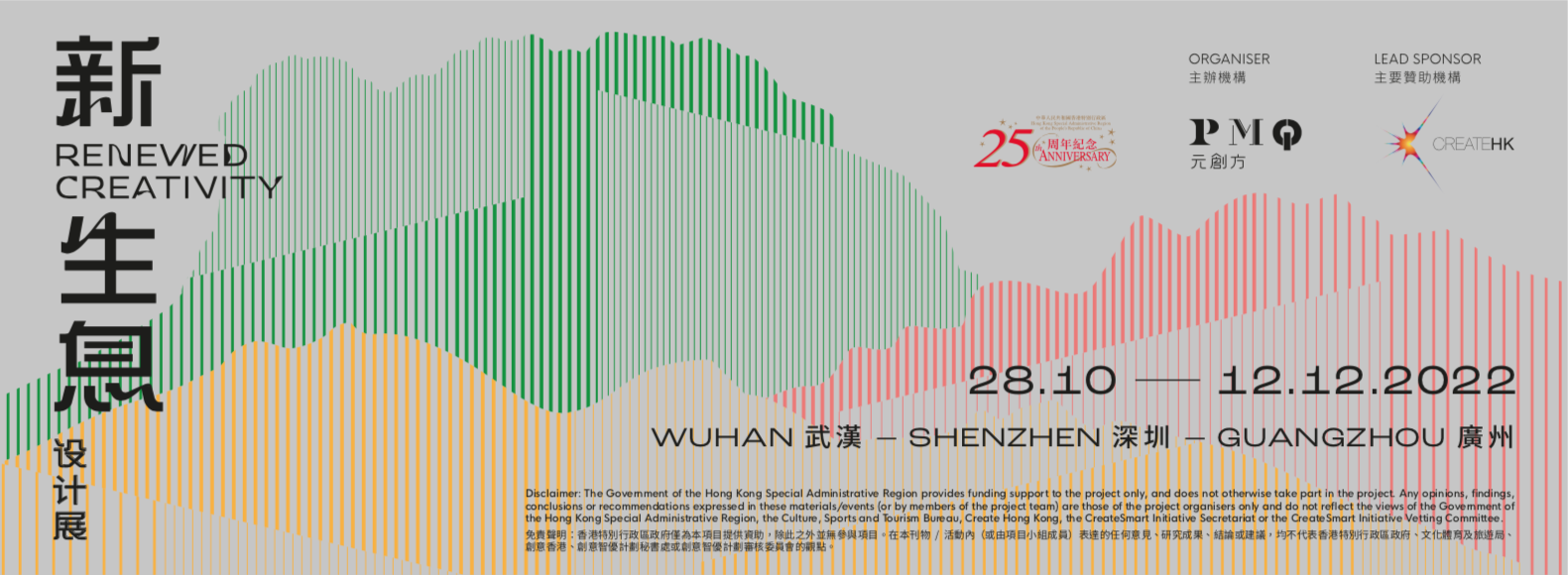心源澄静自然而然
2017年对刘建国的绘画艺术注定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质变年。那一年,他创作了反映藏胞生活的《晨曦》(120x40cmm)、《格桑花》(140x69cm)、《虔心之路》(120x40cm)等系列作品;那一年,他的作品凸显出澄净内心的画风,创作心境倔强而又高傲。
《澄静》
《澄静》(69x69cm)可谓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幅再简单不过的作品:画面上只有藏族母女俩的静态肖像。没有任何背景,但不是没有情景;没有一个情节,但不是没有故事;没有丝毫刻意,但不是没有诗意;没有半句说词,但不是没有语境。母女俩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一脸澄静内心的表情,让人浮想联翩,意味无穷。澄静的清澈之意,平静之态,安静之状,恬静之美,“此虽眼前语,然非心源澄静者不能道”(宋罗大经《鹤林玉霞》卷十六)。这是“血脉澄静”(《韩诗外传》卷七),是内心深处的本性与价值。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在《司理弟之官岳阳相别于定王台凄然有感为赋五诗以饯其行》中,有“心源本澄静,皎月悬晴空。利欲一泊之,晶明变尘矇”的诗句。刘建国以《澄静》为题所表达的是这样的意境吗?藏胞母女那传神的目光,让我们感受到她们的心境是那样的平淡,她们的心灵是那样的纯净,他们入世的胸襟具有大地般的宽厚,他们生活的信仰具有大山般的坚韧。看到这些,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南宋诗人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名句。谢脁写的是登山临江所见到的春晚之景以及遥望京师而引起的故乡之思,而画家带给我们的是不为外物所惑的质朴与勇气,创作的心境犹如“一池澄静暮痕清”(龙池二绝的前句是“尽道神龙此有灵),远离喧嚣的生活就是这样原汁原味,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画家把藏胞纯粹的生活美、质朴的人性美、澄净的心境美,浓缩成一副亲切而平静、平凡而伟大的图像。母亲那仁慈善和的脸容,眼神里有点疑惑,有丝忧虑,有份无奈,更多的是对关切、关心、关爱不露声色的感念;被母亲搂抱在左怀的女童,一张稚嫩的成长脸上,一对清澈的大眼睛,似乎在张望一个陌生的世界。她们好像远离尘世的天地,从一个没有喧嚣的世界出来,遇到不熟悉的面孔,看到不知晓的事物,听到不习惯的询问,这一切的一切,在澄静面前是那么格格不入。如果说绘画被当作艺术家思想的产物,那么,自然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反映生活与变化的自然效果是刘建国作品的主格调。尽管绘画前他是处于置身事外的境界,但遇到自然而然的生活景象,就会激发出艺术创作与表达的灵感,催生出捕捉他们并创造景象的冲动,所以说,他的画不是依赖对形式可以的记忆,画面的形成是自然的。
画家的心无旁骛,画家的心性纯粹,凝聚在笔端,融入了画意。沉浸在水墨世界的超然,不为外物所惑的内心澄净,滋养着关注事物真实的绘画理念。那些人,那些事,那个地域,那种场景,不仅是真实的存在,而且走进了内心,具化为内在世界的映像。当某个时刻受到某种启示的激发,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心境抒发,或是一种思想的阐述,或是一种思考的诠释,或是一种思虑的表达。《格桑花》便激发了他开心歌唱的艺术心境。
《格桑花》
这是一个喜兴而又深情的画面。一老一少两个藏族女性,站在格桑花生长的土地上,或许是个路口,或许是个驿站,或许是面山坡,或许是在屋角,似乎在等待什么,又像在迎候着谁。面对我们的是一位藏族姑娘美丽甜蜜的笑脸,洋溢着幸福吉祥的喜气;她右臂后是一位身躯健朗的藏族妇女(或许就是她的母亲)的背影,穿着厚厚的藏袍,露出的半边脸上戴着口罩,她用宽实的臂膀刻意为身后的孩子遮挡着风寒。画家的笔墨就是这样透过画面上两个藏族女性的形象行为和情感流露,极尽艺术语言诠释着格桑花的品格和精神。格桑花是雪域高原最美的花。农舍旁、小溪边、树林下、山坡上、草坪中随处可见,千百年来顽强地繁衍生息在高原这片土地上,历经岁月沧桑,风雨愈疯狂,身姿越挺拔;日照越强烈,开得越灿烂;就像守护神一样守护着勤劳善良的藏族人民。
对格桑花的歌唱是藏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是雪域高原人民心中的精神象征,藏族人民心中永远的追求。刘建国以《格桑花》为画题,把格桑花的寓意赋予藏族姑娘的姿容笑貌,赋予藏族女性的生活本真,赋予雪域高原的生命,抒发画家美好祝福的情感,也抒发出自己满腔喜悦的艺术情怀。喜兴是生活的主旋律,是画家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感受,对时代的认知。毋容置疑,没有对格桑花蕴含的文化了解,就读不懂《格桑花》的艺术表达,也读不懂画家的心源心境。
绘画艺术的世界更奇妙
艺术道路的回望常常让人忐忑不安。当把镜头拉回到2015年刘建国的绘画创作,会感受到一种多姿多彩的表达凝重。
《圣路》(180x190)就是这一年的作品。看似笔墨雄浑,却掩饰不住画家内心的些许焦灼:为艺术表现的题材,为画中人物的命运,为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奋斗,为他们的情趣,也为他们时有的不知所措?人物占据画面,有向往的远空,却没有阳光的指引;有心往的圣路,却没有通向的途径。他们在行进,脚下却没有道路。画中人物心中都有一个虔诚的向往,都怀揣着一个在圣路前行的梦想。但画面上却只有他们在向来时路的祈祷,在向去往路的探望。他们向往圣路,却找不到通途;他们找寻圣路,却心中迷茫。就像那些朝圣者,为祈望的美丽叩拜在漫长的路途,不惜光阴与生命,只是《圣路》的人物多了几分心绪的神秘,几分困惑的迷茫。
《圣路》
可不是吗。在画家的笔下,呈现出奔向圣路的一片萧瑟疏离,迎面扑来的是一派荒凉之感,迷惑之神。画面看似繁复。人物的心绪繁杂,情境的空间繁纷,线条的墨色繁琐,但繁而并不觉得乱,反倒让人觉得画家酣畅地表达了内心的不平静。我们栖息的世界虽然千奇百怪,可在画家的哲学思想里,却不外乎两个对立面:或是生与死,或是静与动,或是有与无,或是苦与甜,或是美与丑,或是富与贫,或是阴与阳,或是平凡与伟大,如此等等。如果这是一个理想的梦境,绘画艺术更在意如何去描述出他们的本质,把画面滲入到观众的思想中。这需要艺术来诠释、描绘出逼真的梦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栖息的世界还没有绘画艺术的世界奇妙,没有画家灵感深处逼真的梦境诡异。当然,这不是所有绘画艺术家都认同、都具有、都追寻的梦境,要看绘画灵感来自哪里!
憧憬远方梦,难舍来时路。《圣路》的灵感来自一个路遇的“朝拜”情景,一个眼见为实的感动。画家融进对藏族人民心性纯朴的偏爱,对信仰虔诚的敬仰,艺术地再现了信徒们朝拜路上的景象。她们本是一道风景,但他们虔诚得看不见别人看他们的眼神;而我们渴望成为一道风景,她们却不屑一顾心外的景色。哪里的天空哪里的人,那方地域那种文化,都是对心灵的净化。读过这幅作品,有人总赞叹画作笔力熟练。刘建国却是因为“熟”而更加随性自然,一种纯熟后的率真之气,每一笔完完全全发自内心,绘画技法与自然道理融合一起,使每一幅优秀作品都不会有相同的痕迹。
但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刘建国在这个时期绘画心境的凝重。在这一年他的创作中,画面上的人物表情犹如他的心境,很冲动,却不开心;很纯粹,却不满意;很理想,却又乏力;很尽心,却又无果。《煨桑》(180x190cm)就是一幅这种心境状态下的作品,画中人物的表情都是那样的凝重。煨桑是藏民族最普遍的一种祭天地诸神的礼俗,他们用松柏枝焚起蔼蔼烟雾,希望神仙能降福敬奉他的人们。《煨桑》的画面信息丰富,场景震撼,人物个性铭心刻骨。远景的天宇与雪景,中景的风幡与面具,前景的人物与姿态,既在表达这种仪式的庄重与神秘,也在渲染藏家儿女的祈愿与期盼。在藏族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桑炉,藏历新年初一,人们第一件事就是煨桑祭神。但刘建国创作的《煨桑》却打破了空间、时间、地域的概念,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画作在广东展馆一亮相,强烈的视觉冲击引起热情反响。被北京一家著名商户拍走收藏。后来,每当举办刘建国反映藏族生活主题的画展,都要去哪家收藏商户借画。
《煨桑》
画如其人,画如其心。刘建国的创作大多是表达自己的感受,生活的感受,时代的感受,物像的感受,心灵的感受。画面是画家的心境语言。他的每一幅画都有激情点,这就是表达对象触动自己的地方;每一幅都融入了画家的心境、情绪、思想、灵感。这与迎合社会心里而言,抑或趋利社会时尚而论,刘建国都是那种格格不入的画家。在绘画学习成长时期,艺术追求的心扉大开,受着各种情感的刺激,呼吸着新鲜的学术空气,分享完导师以身作则地指点,再去看天南海北的画展;完成了忐忑不安的课业,就在奇思怪想的圈子里过滤理智;流览过多姿多彩的画坛风景,又回到笔墨技艺的研习。如果说艺术家的情操要有激动心灵的力量,必须有完美的形式来做他的外表,那么,在作品中表现艺术的纯粹和生活的虔诚便是他艺术追求的美丽。也因为如此,刘建国在画面上留下的符号总是能与观众建立起直接而难忘的联系,作品反映出现代生活的速度与活力,现代人的秉性与情绪,是他不假思索的感情倾泻,珍重具有个性特征的能力不仅使他成为一域水土上的一个好画家,还使他在亦步亦趋的前行中上升为这个时代可圈可点的艺术家。
敬畏平凡的人文情怀
每个书画家都有自己的艺术生态环境。刘建国也不例外。这位出生在河南修武的70后,从师范学院到师范大学,从专科、本科到获得河南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从中国美协人物画高研班到中国国家画院的高研班,师从中国国家画院导师陈钰铭先生的刘建国,在平凡的生活背景和环境中,文化素养和绘画艺术智识伴随着他的人生成长日积月累。
不得不说,刘建国是敬畏平凡的受益人。他创作的《乡戏》(120x240)就让我们对平凡的乡土文化生活有一种重温的新奇与亲切。在好似村户人家屋后柴火堆与皑皑白雪覆盖山丘的模糊背景中,朝我们走来的两个汉子,一身闲暇出门的行装,一副硬朗健壮的身板,一脸惬意自足的表情,一种闲适轻松的姿态。他们是谁,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画家在画题中回答了。而在画意中回答的是你我心中或许有、口中却还无的疑虑,还有灵魂的拷问。画家热爱并流连在平民生活的场景中,在田间耕作劳累间歇的季节,闲暇时日三两成行去看《乡戏》洋溢在脸上的自满,生动地描绘出农民朴质的生活本性。刘建国的作品就是这样,构图并不复杂,人物什么时候都处在主导地位,他们的身份、心境、情感,他们的生活状态、性格、感受,他们对世界的认知、理解、依存,他们在自然空间生存的无畏无惧、执著前行,都在人物丰富多彩的形态中,都在笔墨自如的技法中,都在看似漫不经心的画意中。
《乡戏》
刘建国是那种不善言笑的严谨人,犹如他对绘画艺术一样,一丝不苟地创作每一幅作品,处理每一个细节。但千万不能因此而误以为少于言笑的严谨是缺乏激情,恰恰相反,他对乡土气息有着深刻感悟的情愫,对耕耘在黄土地的平凡有着深厚敬仰的情怀,他把表现凡人喜怒哀乐的情感和揭示他们对乡土生活热爱的情愫,内化为粗旷而厚重的笔墨,具化为对天地敬畏和对平凡歌唱的画面,形象的呈现并诠释了自然的伟大、灵魂的高贵、意志的坚韧、性格的善良、人文的血脉。他的那些作品中弥漫的人文情怀,那些题材表达的人文关怀,那些场景呈现的人文景象,那些画面营造的人文氛围,那些意境创造的人文情绪,那些人物蕴含的人文血脉,无一不是在用绘画艺术阐发人文、诠释人文、具化人文,宣泄他审美意识中丰富多彩的人文感受。
刘建国的人文关注都在他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好像是在用绘画艺术记录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这是生活的世界,也是心灵的世界;是原生态的生活,也是艺术发掘的生活。这里有形形色色的景象,让画家们浮想联翩,让画笔出神入化,让墨色变幻莫测,让画意韵味丰富,让画面生机勃发。刘建国选择了关注平凡。这不仅是他创作题材的选择,也是创作主题的表达。在他的作品里,无论人或事,无论情或景,无论物或像,都泛滥出浓郁的乡土平凡,尽管平凡得微不足道,但却朴实无华。乡土入画表达的是一种深厚的情结,一种人文的思念。在不知不觉中,刘建国的创作形成了乡土主题的格调。反应中原农民生活的《农耕》,反应西北牧民生活的《高原清风》,反应巴蜀民众生活的《蜀味》系列,反应高原藏胞生活的《晨曦》,他把艺术创作的目光落在乡间平民的生活,把绘画主题集中在对平凡的关注。他把那些平凡演绎得多姿多彩,寓意深长。对一个优秀画家来说,这绝不是一个绘画艺术选题的单纯偏好,而是绘画艺术心境的流露。
《晨曦》
对平凡人个性的准确把握,是刘建国乡土主题画的突出特征。那些画面充满了动感,即使是静态的描述,从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也是不同的灵动。画面上人物虽然平凡,但他们的视线却总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这让你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画家处在从下往上看的仰视地位。这样的视角语言似乎在告诉我们:平凡是多么的让画家敬畏!平凡是多么的让艺术敬畏!他在凝视那些平凡,也在赏析那些平凡的美丽;他在仰视那些质朴,也在仰望那些质朴的境界;他在关注那些生活,也在表达对那些生活困惑的思考;他在关切那些地域,也在描述那些地域生生不息的精神。“对平凡人、平凡事的敬畏是绘画艺术的境界”。这既是刘建国的切身感受,也是经验之谈。
绘画艺术的创作生活中越是平凡无奇的普遍现象,往往越能体现出普遍的真理。刘建国的那些画作,没有预定的主题,没有设想的主调,走出家门,在门户外实景实地面对面地现场创作,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的大不相同在于,没有人为的受控,艺术家的灵感、意志都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不断变化。画家根据自己对社会对生活对自然对事物的观察、感受、理解和认知,能看到别人不能看到的、想到别人不能想到的、表达出别人不能明确表达的思想、愿望、心境和喜、怒、忧、乐、甘、甜、苦、悲等情感,就是独创的智慧。这需要艺术家有份坚韧执着的追求,有双洞若观火的眼睛,有种异想天开的灵感。
《虔心之路》
他是那种极少不停留在某个固定绘画模式中的青年画家,这并不是他的创作艺术游离不定,而是他总在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不断校正自己,所以他的作品在不断进步中成熟发展,如同他的生活一样富有情怀,富有内涵,富有韧性,富有意味,富有节奏,富有系统,也好似他的智识一样渊博,一样灵通,一样深厚,给人的是一种纯真而严肃的美,平凡而高尚的美。这种美同样是一种和谐,艺术的内容与画面的和谐,笔墨的流畅与韵味的和谐,画家的质朴与意境的和谐。没有什么比画家与创作的心契神合更美了。